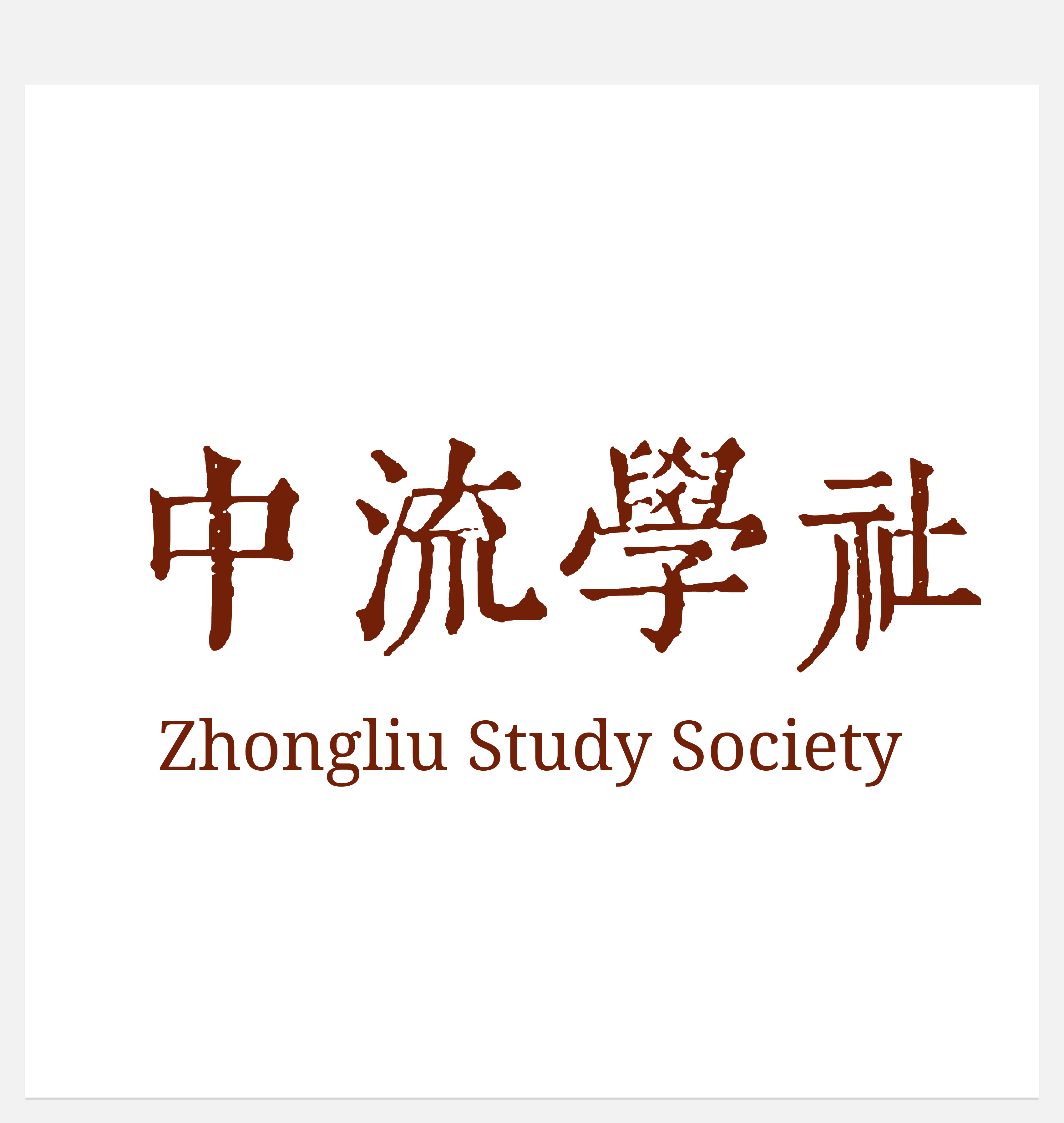阿尔都塞:在废墟上的最后独白
阿尔都塞:在废墟上的最后独白
中流学社阿尔都塞:在废墟上的最后独白
希望重新复兴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或是人的解放视为历史的目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样的目的论便走向了破产。一直以来,物化-解放仿佛就被认定为一个必然的逻辑链条。就比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隐晦地表达了将人的解放视为历史的目的。而他所追溯到的根据显然就是《1844年手稿》中所强调的“人的本质的复归”。
在五月风暴前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敏锐地抓住了目的论的逻辑问题。人通过选择定义自己,在无目的的世界中反抗荒谬亦或是投入社会实践来赋予自身意义,这个意义不被先验地预设。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定要坚持某种历史决定论,那么它和讲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然而,如此这般把自由行动无限抬高的存在主义,已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梅洛-庞蒂还是萨特都逐渐认识到这点。梅洛-庞蒂开始引入结构概念来调和主体与结构。遗憾的是,当萨特晚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时,他试图将存在主义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是人学的空场”)的努力,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存在主义的本体论根基。
1960年和1961年,加缪和梅洛-庞蒂相继与世长辞。与此同时,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回应也走向了它的黄昏。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燃起了结构主义的烈火,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的《资本论》研讨班让萨特的新书也黯然失色。登上舞台的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十年到来了。
“理论反人道主义”如利剑般直指存在主义。阿尔都塞宣称把马克思主义从人道主义中“解救”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科学,而非人的本质。他把卢卡奇希望回溯的“青年马克思”定性为“意识形态”,以此与“科学”对立起来。在阿尔都塞眼里,历史作为无主体的过程必然由多元决定的结构驱动,而不能还原为单一矛盾的展开。他将萨特的存在主义批评为“主体目的论”,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幻象。
1968年的五月风暴如同从空无中爆发一般地打碎了这一切。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怒吼声打破了香榭丽舍大街的虚假繁华。但与此同时,“结构不上街”、“阿尔都塞无用”的旗帜,也终结了结构主义的那十年。早期阿尔都塞试图用那种超然的结构分析一切,最终却无法解释自身理论何以可能。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建造了一艘精密的哲学潜艇,但是忘记设计了舱门,最后他自己走向了窒息。
阿尔都塞的晚年是孤独的。五月风暴的狂潮之下,他的战友拉康、福柯、巴特甚至学生朗西埃都相继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他。1974年,阿尔都塞出版了《自我批评集》。1980年,精神分裂的他误杀了自己的妻子。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成为了他最后的哲学呐喊。
他直接性地跳过了黑格尔,回到古希腊去对话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寻找原子论唯物主义的传统。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仍然是他的思想源泉。借助他们的思路,他重申了相遇的唯物主义和无主体的哲学概念:世界的构成和重构,是原子在虚空中随机偏移、不断碰撞的产物。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要素在偶然条件下所结合而产生的。就这样,无意义的历史在一次次偶然的相遇中产生了意义。历史没有预设的主体,而是偶然事件和力量的临时聚合产生了国家,产生了社会,而国家和社会也终将面临解体的命运。
但这最后一搏是无力的,他未能摆脱个体的悲惨命运。阿尔都塞偶然地登上了他给历史描绘的那列无终点的火车,他也被永远困在了火车里。当他在虚空中追问偶然的意义时,是否听见了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笑声?恍惚间,他是否还会怀念在巴黎高师叱咤风云的日子?阿尔都塞还是死了,他的思想一次次地死在了他的躯体之前。
一个天才的号手殒命了。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今天或许是其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解放的开始,从而成为其重生变革的开始。”(阿尔都塞语)
也许唯有历史的弦音仍在追随这位号手远去的背影。
这列火车仍在虚空中行驶着,下一站的站名还没有被书写。